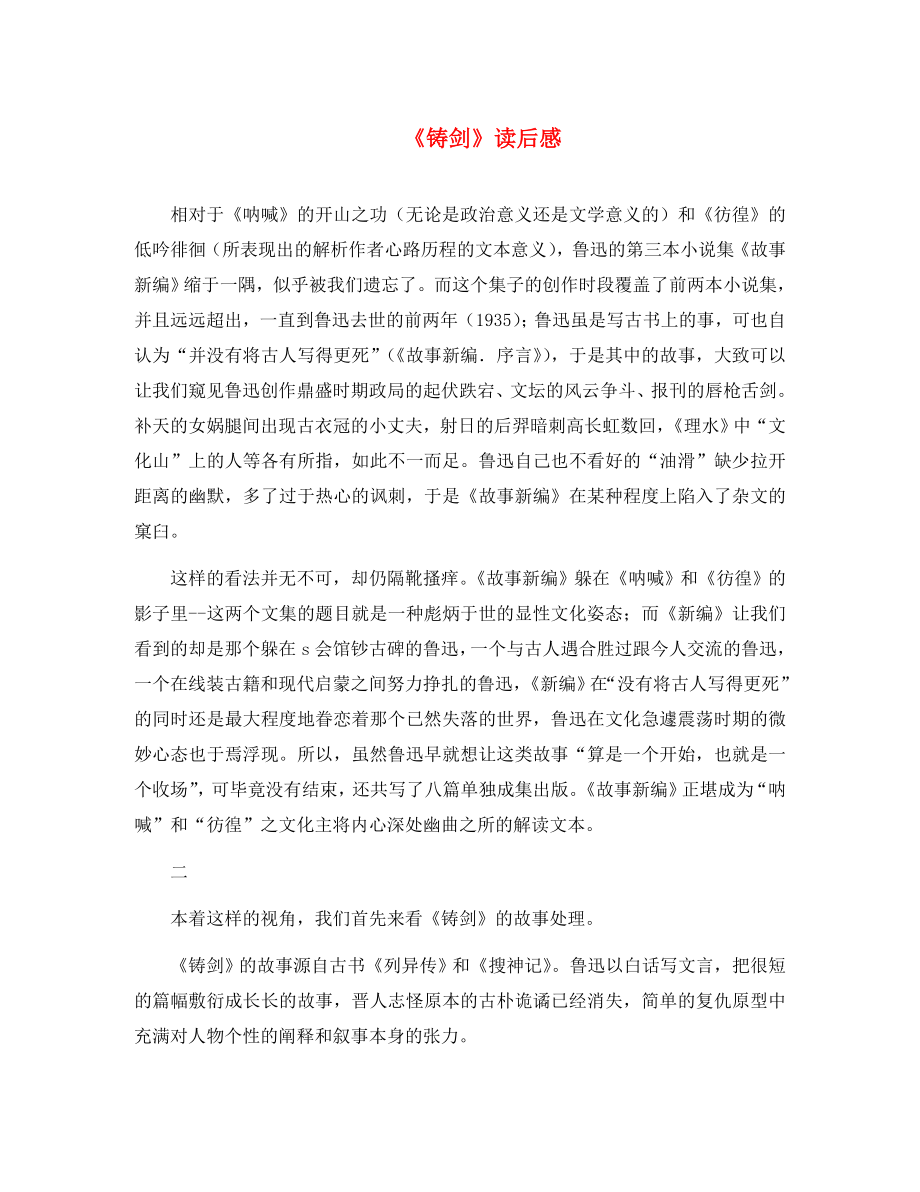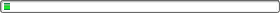《九年級(jí)語(yǔ)文上冊(cè) 第二單元 3《鑄劍》讀后感 長(zhǎng)春版(通用)》由會(huì)員分享�����,可在線閱讀��,更多相關(guān)《九年級(jí)語(yǔ)文上冊(cè) 第二單元 3《鑄劍》讀后感 長(zhǎng)春版(通用)(3頁(yè)珍藏版)》請(qǐng)?jiān)谘b配圖網(wǎng)上搜索����。
1�、《鑄劍》讀后感
相對(duì)于《吶喊》的開(kāi)山之功(無(wú)論是政治意義還是文學(xué)意義的)和《彷徨》的低吟徘徊(所表現(xiàn)出的解析作者心路歷程的文本意義),魯迅的第三本小說(shuō)集《故事新編》縮于一隅���,似乎被我們遺忘了����。而這個(gè)集子的創(chuàng)作時(shí)段覆蓋了前兩本小說(shuō)集����,并且遠(yuǎn)遠(yuǎn)超出����,一直到魯迅去世的前兩年(1935)��;魯迅雖是寫(xiě)古書(shū)上的事�,可也自認(rèn)為“并沒(méi)有將古人寫(xiě)得更死”(《故事新編.序言》),于是其中的故事�,大致可以讓我們窺見(jiàn)魯迅創(chuàng)作鼎盛時(shí)期政局的起伏跌宕、文壇的風(fēng)云爭(zhēng)斗�、報(bào)刊的唇槍舌劍。補(bǔ)天的女?huà)z腿間出現(xiàn)古衣冠的小丈夫��,射日的后羿暗刺高長(zhǎng)虹數(shù)回��,《理水》中“文化山”上的人等各有所指�,如此不一而足。魯迅自己也不看好的“油滑
2�、”缺少拉開(kāi)距離的幽默,多了過(guò)于熱心的諷刺�����,于是《故事新編》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雜文的窠臼����。
這樣的看法并無(wú)不可�����,卻仍隔靴搔癢?���!豆适滦戮帯范阍凇秴群啊泛汀夺葆濉返挠白永?-這兩個(gè)文集的題目就是一種彪炳于世的顯性文化姿態(tài);而《新編》讓我們看到的卻是那個(gè)躲在s會(huì)館鈔古碑的魯迅����,一個(gè)與古人遇合勝過(guò)跟今人交流的魯迅,一個(gè)在線裝古籍和現(xiàn)代啟蒙之間努力掙扎的魯迅��,《新編》在“沒(méi)有將古人寫(xiě)得更死”的同時(shí)還是最大程度地眷戀著那個(gè)已然失落的世界��,魯迅在文化急遽震蕩時(shí)期的微妙心態(tài)也于焉浮現(xiàn)����。所以,雖然魯迅早就想讓這類故事“算是一個(gè)開(kāi)始����,也就是一個(gè)收?qǐng)觥?���,可畢竟沒(méi)有結(jié)束�����,還共寫(xiě)了八篇單獨(dú)成集出版�。《故事新編》正堪成
3�����、為“吶喊”和“彷徨”之文化主將內(nèi)心深處幽曲之所的解讀文本����。
二
本著這樣的視角,我們首先來(lái)看《鑄劍》的故事處理�����。
《鑄劍》的故事源自古書(shū)《列異傳》和《搜神記》�����。魯迅以白話寫(xiě)文言,把很短的篇幅敷衍成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故事�����,晉人志怪原本的古樸詭譎已經(jīng)消失��,簡(jiǎn)單的復(fù)仇原型中充滿對(duì)人物個(gè)性的闡釋和敘事本身的張力�����。
原本的故事��,父子兩代的篇幅是大體均等的���。而在《鑄劍》中,真正的鑄劍者在故事開(kāi)始的時(shí)候業(yè)已死去����,他的事跡是通過(guò)小說(shuō)主人公眉間尺的母親之口交待的:
“大歡喜的光采,便從你父親的眼睛里四射出來(lái)�����;他取起劍����,拂拭著�����,拂拭著�。然而悲慘的皺紋����,卻也從他的眉頭和嘴角出現(xiàn)了。他將那兩把劍分裝在兩個(gè)匣子里��。
…
4�����、…
“‘你不要悲哀����。這是無(wú)法逃避的。眼淚決不能洗掉命運(yùn)��。我可是早有準(zhǔn)備在這里了���!’他的眼里忽然發(fā)出電火似的光芒�����,將一個(gè)劍匣放在我膝上��?!@是雄劍?����!f(shuō)����。‘你收著�。明天���,我只將這雌劍獻(xiàn)給大王去����。倘若我一去竟不回來(lái)了呢����,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間了。你不是懷孕已經(jīng)五六個(gè)月了么?不要悲哀����;待生了孩子,好好撫養(yǎng)�。一到成人之后,你便交給他這雄劍�����,教他砍在大王的頸子上��,給我報(bào)仇����!’”
這是莊嚴(yán)的筆調(diào),是魁梧的人格��,是反抗者的頌歌�����。眉間尺的父親是真正的英雄�����,是作為其子的“史前史”而出現(xiàn)的,故事如此安排已不僅僅是敘事技法方面的問(wèn)題了��,魯迅的匠心在于拉開(kāi)英雄和現(xiàn)實(shí)之間的距離�����,樹(shù)立一個(gè)理想寄寓之所�����,告訴我們真正的
5�����、安身立命所在�����;《列異傳》和《搜神記》沒(méi)有這么明確的目的����,因?yàn)樯褊E在其中是不證自明的�;而《鑄劍》中的父親則是魯迅親手發(fā)明的神話,是附魅傳統(tǒng)經(jīng)過(guò)現(xiàn)代理性反思破滅之后新的(舊的��?)夢(mèng)想,神話的時(shí)代畢竟已經(jīng)過(guò)去了:
“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驟然失去了光輝�����,惟有青光充塞宇內(nèi)�。那劍便溶在這青光中,看去好像一無(wú)所有�。”
魯迅也只能說(shuō)“看去好像一無(wú)所有”�����。他筆下的英雄人格在現(xiàn)代題材里幾乎沒(méi)有出現(xiàn)過(guò)��,涓生�����、呂緯甫����、魏連殳都是失敗的知識(shí)分子、文化精英����,帶著絕望的氣息��,更遑論閏土和阿Q這些農(nóng)民們���;英雄只在古書(shū)里,是(故事“新”編的主人公)眉間尺(我們毋寧將他看作是“現(xiàn)在時(shí)”的)的父親�����;照理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魯迅從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開(kāi)始��,就應(yīng)該是最有資格和最堅(jiān)定具備審父意識(shí)的人�,但是魯迅實(shí)在不能夠堅(jiān)定。雄劍溶在青光中看似全無(wú)��,正隱約象征魯迅心底深處對(duì)文化�、對(duì)國(guó)家命運(yùn)虛無(wú)主義的態(tài)度。
 九年級(jí)語(yǔ)文上冊(cè) 第二單元 3《鑄劍》讀后感 長(zhǎng)春版(通用)
九年級(jí)語(yǔ)文上冊(cè) 第二單元 3《鑄劍》讀后感 長(zhǎng)春版(通用)